
编者按:如果说培养优等生是教育的常态,那么让基础薄弱的学生实现跨越式成长,才是教育智慧的闪光。大庆左思高中自建校以来,始终秉持“精准赋能、个性成长”的育人理念,通过“包保制度”的个性化辅导模式、“严慈相济、科学引导”的管理体系,以及“不放弃每一个学生”的教育初心,帮助无数学生突破自我局限,在高考中书写“低进高出、低进特出、高进优出”的成长答卷。从今天,我们陆续走进2025届毕业生的故事,一同感受左思高中如何让“平凡” 蜕变为“不凡”。

“查分那天,手指在‘查询’键上悬了半分钟,生怕看到的数字会让三年努力打了水漂。”付诗杰笑着回忆,直到499分的数字跳出来 ——比模拟考*高分多了20分,稳稳超过特控线,他才敢相信,那个高一数学考78分(满分150)的自己,真的做到了。
电话那头,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:“早说你能行吧,看你天天凌晨亮着的台灯,没白熬。”挂了电话,付诗杰走到窗边,突然想起三年前拖着行李箱报到的那天——手里攥着刚过线的录取通知书,看着公告栏里“优秀毕业生光荣榜”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“我能像他们一样吗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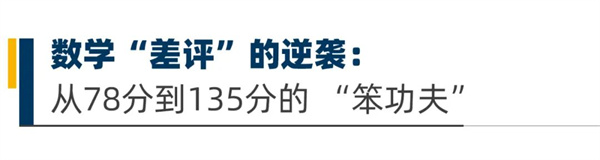
高一上学期的期中考试,是付诗杰高中生涯的**个“坎”。数学卷上的红叉像密集的网,78分的成绩排在班级倒数第五,他把试卷揉成一团塞进桌肚,晚自习时躲在操场角落偷偷哭了 ——“函数图像像天书,立体几何转不动脑子,感觉自己天生不是学数学的料。”
转机藏在数学老师王老师的一句话里。那天课后,王老师叫住他:“付诗杰,你不是笨,是没找对拆题的法子。”第二天,王老师递给他一本“解题手册”,扉页上写着“复杂题 = 3 个简单题的叠加”。手册里,一道圆锥曲线大题被拆成“找焦点坐标”“列联立方程”“算判别式”三个小步骤,每个步骤旁都标着“基础知识点链接”。
“就像把一团乱麻剪成三段,突然就看清了线头。”付诗杰开始了“笨鸟先飞”的日子:每天清晨6点,宿舍还没亮灯,他就揣着错题本到操场角落,借着路灯看前一天的错题;课间十分钟,别人去接水聊天,他抱着卷子往数学办公室跑,被同学打趣“王老师办公室的编外成员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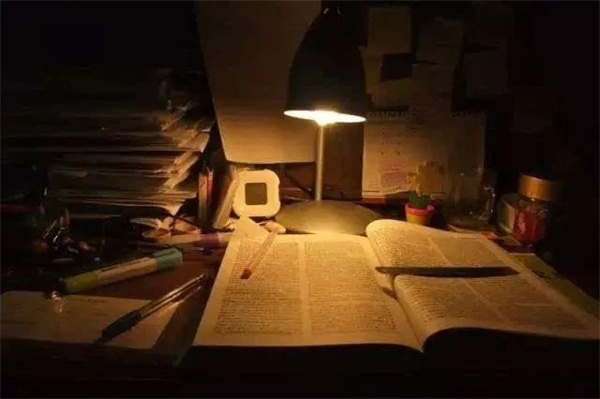
真正的突破,藏在五页草稿纸里。一道高考**的圆锥曲线题,他卡了三天——从课堂听到课后,从晚自习琢磨到睡前,草稿纸写满了五页,步骤改了七八遍,还是卡在*后一步。第三天晚自习,王老师留下来陪他一起推导:“你看,这里忽略了隐含条件,就像搭积木少了一块底座。”那天晚上,他在教室待到凌晨,月光洒在草稿纸上,当*后一步的结果和标准答案对上时,他忍不住在空荡的教室里喊了一声“成了”。
从那以后,他的错题本变成了“三阶秘籍”:左侧抄题,中间写正确步骤,右侧专门记“错因”——“这里漏看了定义域”“公式记错了符号”。高一期末,数学考到115分;高考时,这个曾经的“弱项” 成了强项,考出 135 分。“原来没有学不会的知识,只有没下够的功夫。”

高三一模,付诗杰摔了个 “大跟头”—— 总分比预期低 50 多分,数学甚至退回到90分。拿着成绩单,他**次怀疑:“是不是真的到极限了?”那天傍晚,他在操场蹲了很久,直到班主任路过,递给他一张便利贴:“黎明前的夜*黑,但星星也*亮。”旁边还放着一杯温热的奶茶。

班主任尹大钊老师陪同高考
回到教室,同桌和他说 :“我上次比你还惨,现在不也缓过来了?”从那天起,两个人约定:每天晚自习后多留半小时,互相抽查单词、讲数学题。有次冬夜,两人为一道数列题争得面红耳赤,草稿纸画得像涂鸦,直到找到解题思路时,才发现窗外飘起了雪,“路灯把雪照得发亮,那一刻觉得,再难的题也扛得过去。”

妈妈的短信也成了“解压阀”。一模后,妈妈没问分数,只说:“周末回家吧,给你做糖醋排骨。”回家那天,饭桌上妈妈一句话没提考试,只讲她上班时遇到的趣事,临走时往他包里塞了个保温杯:“晚自习冷,多喝点热水。”付诗杰后来才知道,妈妈那段时间天天给班主任打电话,就想知道他有没有垮掉,却从没在他面前露过一句担忧。
“那些时候才明白,我不是一个人在拼。”付诗杰说,是便利贴上的字、保温杯的温度,让他在想放弃时,总能重新拿起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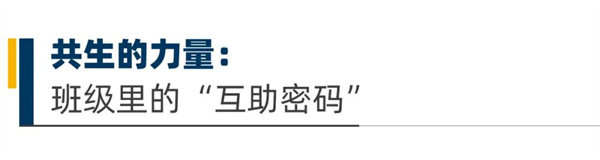
付诗杰的书桌抽屉里,藏着一本“共享笔记”—— 封面上写着 “左思学科互助小组”,里面是四个同学轮流写的知识点总结:他整理的文言文虚词用法,同桌的数学导数题型,前排男生的物理受力分析口诀,后排女生的英语作文模板。
“高一刚来时,我以为高中就是‘各学各的’,没想到这里是‘抱团往前冲’。”付诗杰说,班级里没有“藏着掖着”的竞争,反而有 “共享共赢”的默契。晚自习前,前排同学会把当天的重点笔记投影在白板上;谁有不会的题,往小组群里一发,总有三四个人秒回“我会,给你讲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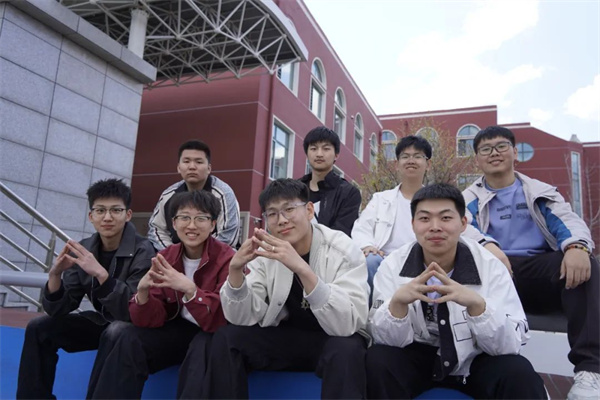
*让他难忘的是“学科互补结对” 活动。他帮英语薄弱的同桌改作文,逐句标出错处:“这里时态错了,应该用现在完成时”;同桌则拿着他的数学错题本,用三种颜色的笔画图:“你看,这个函数图像旋转 90 度,是不是就好懂了?” 三个月后,同桌的英语提了 20 分,他的数学又进了一步。“就像两个人踩着对方的肩膀往上爬,谁也没落下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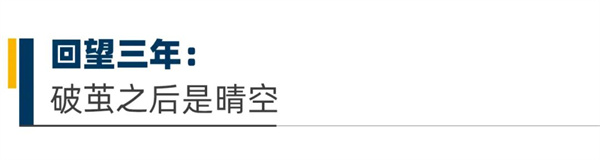
高考结束那天,付诗杰在教室*后一排的墙上,找到了自己高一写下的心愿卡:“希望数学能及格,考上本科就好。” 如今,这两个目标都成了“过去时”——他不仅超了特控线,还报了心仪的理工科大学。
“如果用三个词形容高中,就是‘破茧’‘同行’‘星光’。” 付诗杰说,“破茧”是和数学较劲的日子,痛但值得;“同行”是老师的耐心、同学的陪伴,暖且有力量;“星光”是凌晨的路灯、深夜的台灯,还有那些在黑暗里支撑他的善意,“它们看起来微弱,聚在一起就成了照亮路的星河。”

对于学弟学妹,他*想分享的是自己的“错题本哲学”:“别害怕错题,它们是帮你找出漏洞的路标。也别孤单,左思的教室里,永远有人和你一起刷题、一起进步。”
至于未来,付诗杰笑着说:“大学想继续学数学,这次要主动和它‘做朋友’。” 毕竟,那个曾经被数学难哭的少年,早已在破茧的疼痛里,学会了拥抱风雨的勇气。